 下载文档
下载文档
一翻微信通讯录,学生们发现,费梁的头像和名字换了。面带微笑的个人照变成了盈盈秋色,名字改成了妻子的名字“叶昌媛”。
顿了一秒大家才回过神:费老离开有段时间了,到今年6月,恰满一年。
照片里的那几抹金黄,是费梁和叶昌媛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里看了无数次的风景。
过去的六十余年里,他们如影随形,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撰文一个整理,一个解剖一个建卡,携手摸清中国两栖动物的“家底”,一起捧回国家自然科学奖,共同创建了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
即便是退休了,两位银发青衫的老人,每天依旧准时上班,一个步子迈得大但缓,一个步子踏得小却快。一高一矮,手挽着手,春去秋来,无间冬夏。
这样的相伴因费梁的突然离世被打破。
当亲朋还在为叶昌媛担心时,上班路上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老人挎着包,默默独行,步伐虽慢仍如从前般坚定。

退休后,两位老人每天依旧挽手上班。张轶佳摄

老伴去世后,叶昌媛独自坚持上班。张轶佳摄
科研搭档一个主外一个主内
费梁走后,叶昌媛开始学着适应,例如学用微信。虽然打字还不习惯,但已能熟练发语音。
叶昌媛眼睛不好,费梁几乎不让妻子看手机,所以对外交流的工作基本由他完成。
“他比我会说”,只要费梁在,叶昌媛就喜欢“缩边边”,依赖着他。一遇到问题,只要叫一声“费梁”,对方就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儿跑来。
他是她的拐杖。每个上班的清晨,从家到单位800多米的路程中,叶昌媛会挽住费梁的手臂,身体微倾,头向他身上靠。费梁瘦瘦的身板总是挺得直直的,一手顾着叶昌媛,一手拎着厚厚的资料。黄昏回家的路上,资料袋里多了新鲜的莴笋、番茄或白萝卜。
“费梁把我照顾得很好”,叶昌媛总说。但与其说照顾,在共同走过的六十余年里,他们各司其职又互为补充。
叶昌媛的优点之一,是记忆力好。“以前我跟着老师胡淑琴工作,她坐在书桌前,一说需要什么资料,我就能立马从书架上找到书,并翻到对应的那一页。”
大部分时间,叶昌媛主内,驻扎实验室,负责标本的整理和资料的收集,而费梁主外,专供野外科考和标本采集。叶昌媛对物种形态特征掌握得更全面,费梁一带回新标本,就给叶昌媛看。哪些特征差异是在变异范围内,而哪些可能是种间差别,她熟稔于心。
每次费梁外出期间,叶昌媛最期待的就是收到丈夫的来信。他的书面写作总是很干净,工工整整。这些“家书”,很少提及自己的生活,谈论更多的是两栖动物的“家谱”,日后也累积成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叶昌媛说费梁“笔杆子”好,费梁觉得叶昌媛“要点把握得更全面”。所以每次写文章她负责初稿,而整理和润色的工作就交予他。

费粱和叶昌媛1979年在四川南坪九寨沟考察。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图
师从大拿 于“白纸”上开始书写中国两栖史
至今,费梁的科考笔记仍然是研究所里学习的范本,也正是因为这一长处,让他获得赏识,从而踏入了两栖动物研究的大门。
上世纪60年代初,二十多岁的费梁和叶昌媛先后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并前后脚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最早他们跟着所里去科考,叶昌媛负责的是两栖动物标本的采集,费梁加入的是小型兽类的考察队。
一个在西坡、一个在东坡,恋爱中的费梁,表达关心的方式,就是和道班工人搞好关系,搭个便车翻过山头,颠簸三个小时去看叶昌媛,或者路过荫蔽潮湿处时,俯身帮她抓几只蟾和蛙。
回到所里,叶昌媛给胡淑琴报告科考情况时,也翻出了费梁帮忙的成果,其详实的记录和工整的书写给胡淑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2年研究所里对研究人员和课题进行了调整,胡淑琴向所领导提出将费梁调到两栖动物组工作,和叶昌媛搭档。1963年,这对搭档成为了夫妻。
实际上,胡淑琴和先生刘承钊也是一对科研夫妻搭档,同样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他们是我国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的奠基人,从50年代开始,就组织和培养后辈,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调查,大致掌握了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区系分布情况。
能到二人手下做事,为国家的科研工作出力,费梁和叶昌媛高兴的同时又深知挑战重重。一走进两位前辈办公室,看到满书架的英文书,他们意识到:“英语,得补。”
那时两栖动物的研究,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书写。任务重、时间紧,野外科考和室内标本工作都得抓,费梁和叶昌媛只能抽空练英语。
他们约定,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整理好后就去实验室,等到食堂开门抓紧吃点稀饭馒头,再到办公室学英语,直至八点上班。这样计划下来,每天基本上能保证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刘承钊和胡淑琴的英文专业书籍就是他们的“教材”,一本接一本地读,遇到生僻的单词就查和背。有的书没法带走或标注,他们就挑有用的部分复印成册。
“胡老师和刘老师都是用英语交流,容不得我们慢一拍。”叶昌媛感叹,环境逼人进取,他们只想离两栖动物的世界再近一点。

1962年9月费梁,叶昌媛于成都。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图
盘清“家底”用脚步丈量两栖动物世界
费梁和叶昌媛对于两栖动物的专注与痴迷,也为儿女创造了专属的童年记忆。
在儿子费翔的回忆里,父母办公室桌子上,总少不了湿漉漉的青蛙。抬头环顾,靠墙的柜子里,更是整齐摆放着一瓶瓶各式各样的标本。桌上的鱼缸里,游动着头部扁扁的蝾螈,地上放置的大盆中,则“盘踞”着一条约一米的大鲵。
家中也被布置成了两栖动物的世界,客厅挂着蛙类和蝾螈的水墨国画,厨房角落的木箱里养着黄粉虫和蚯蚓。父亲告诉他,那是青蛙和蝾螈的食物。
幼时的费翔和姐姐费幼聪经常喂养家中的小精灵,喜欢趴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用显微镜观察蛙卵的细胞分裂。
费翔总羡慕,父亲可以坐上风光的解放牌大卡车,去往那些神秘的深山丛林。长大后他才知道,大卡车只能载费梁到目的地临近的县城,父亲嚼着豌豆和土豆,靠着双腿,丈量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北到冰城南至三亚,费梁根据刘承钊传授的方法,进行细致的摸排和选点,调查两栖类物种的种类、特征、生活史等。
浅滩或急流里,费梁摸着石头过河。一边用脚探稳定的支点,一边弯腰翻动石块,找到蛙类的藏匿之处。亦或侧着身,支一杆网兜,在深水或暗沟里慢慢地掏。
如果附近没有可以借宿的学校或道班,河边宽敞的平地上,就是科考人员的临时“栖息地”。每个人拾几根木棍,撑一张油布,便算搭起了避所。
发现“新朋友”最让人欣慰。但要确定是否为新种,费、叶二人极为严谨。1974年,费梁在湖北利川考察时发现了一只金线蛙,但其和前辈以及湖北学者记述的同类相比,没有声囊。
费梁立马写信给叶昌媛,回成都后两人又一起研究,但并没完全下“新种”的结论。
“到底是这类标本都没声囊,还是只因个体变异而失去了声囊?不能草率。”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叶昌媛记得,1979年,费梁重回利川,而且还出发去了金线蛙的栖息地宜昌、武汉、北京和杭州。在前后采集和对比了上千号标本后,两个人才证实了五年前的猜想,并命名为“湖北金线蛙”。
在2022年《中国生物物种名录》里,中国一共有68172个动物物种及种下单元,两栖动物物种有548种。而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个数字只有两位数。
精确到个位数的“548”,正是刘承钊、胡淑琴、费梁和叶昌媛等科研人员,七十余年来跋山涉水和严谨治学的结果。

1982年3月费梁等在贵州江口县梵净山考察。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图

1982年7月8日叶昌媛工作照。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图
笔耕不辍 一家老小齐上阵写出专著英文版
两栖动物界的“人口”普查不仅是弄清楚“有多少”、“是哪些”,还要“分得清”。
费梁和叶昌媛基于不断丰富的标本库,开始逐步总结、完善、规范和统一标准量度和相关名词。每个物种的头长、眼长、眼距等分别在哪个范围,背上的花纹、疣粒、光泽等各是怎样的特征,哪些是种级差异哪有又是属级区别......他们制定了“一把尺”,便于业内鉴定、参考。
这些成果凝结在了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一书中,于1977年、1990年和2005年更新出版,是科研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费、叶二人也谋划着如何让中国的两栖动物研究“走出去”。“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成果,寻求更多发展。”早在1994年,两人就计划对《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进行增补后编撰成一本英文专著,但后续因为合作上的事宜被一直耽搁。
2007年,费梁和叶昌媛作出决定,全权承担编撰和出版工作。当时幸得所里领导支持,一句“没事,你们出”,让二人更有了信心。
费梁常说,人活的是精神。这句话不止挂在嘴边,为了方便专著的写作和编撰,退休后的他和叶昌媛一起开始学电脑。他们将使用的步骤逐一记录在小册子上,反复练习。对拼音不太熟悉的费梁,用电子手写板写字,一撇一捺都苍劲有力,与用钢笔在纸上书写的无异。
两栖动物骨骼图是英文专著的亮点之一。叶昌媛提到,骨骼与动物机能息息相关,其可以反映动物的系统关系,进化的历史,在分类学上有重要意义。
一套骨骼图的完成可能会耗费十天半月。费梁需对标本进行解剖,并挑干净比针还细的皮肉组织,再将骨骼放置于显微镜下,用相机对着目镜拍摄。以毫米计的软骨和骨间部分没法清晰呈现,他特地跟孙女学了PS修图,以便按比例对骨骼图进行“精加工”。

费梁在电脑上精绘两栖动物骨骼图。杨晨摄
在内容编排上,费梁绘图排图,叶昌媛往框架里“装”文字。他们力求内容完整,保证物种身体各部分的骨骼都有编排展示,头骨、舌骨、胸骨、四肢骨……依次排序。哪些部分需要过细,哪些内容最好合并,两人都有商有量。
为了使专著的英文翻译符合现代英文语法和书写习惯,他们从家中找到了得力的助手:精通英文的女儿,和母语为英语、且还是一名医学博士熟悉专业词汇的女婿。
2007年开始,连续五个夏天,费梁和叶昌媛都会带着一箱资料飞往美国,把办公室搬到女儿家。叶昌媛翻译初稿,女儿和女婿进行精翻和审校。两位老人常挑灯工作至半夜,孩子们心疼,一遍又一遍地催促他们休息。
在努力攻克英文专著的同时,由费梁、叶昌媛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编目,并编著了《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图鉴》《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等专著。这些成果获得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获得殊荣的两年后,两人的第一本英文专著,共计1100多页、近200万字的《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一卷正式出版。

201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5年1月9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图

2014年3月24日两位老人工作照。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图
谦和包容 他们与后辈亦师亦友
《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的编撰和出版无疑又将成为业界的标杆和指南。中山大学博士生吕植桐用“继往开来”形容了这本专著。“又是英文版,想必将影响和帮助到更多热爱两栖动物的年轻人。”
“领路人”,这是众多后辈对费、叶二位前辈的评价。他们是必读专著封面上烫金的名字,是受人敬仰的存在。很多人会慕名前去成都生物研究所,走进“传说中”的243办公室。
那间不过二十几平的房间,是费、叶二人退休后主要办公的场地。靠窗的位置,安放着两张书桌,两老各占一张相对而坐。费梁在左,右手执笔,在写字板上慢笔缓书,旁边摆着标本瓶、解剖镜、显微镜;叶昌媛在右,埋头于“高耸”的书籍和资料,偶尔抬头和搭档交流一句。
一进门的两侧,都立有书柜,里面塞满了他们这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如果提出想要什么资料,两位老人能快速从柜子里抽出。有些零碎的文本也会归纳整理好,用促销传单作为封面装订成册。
更多的“资料”在两位老人的脑海中。“他们清楚地记得标本采集的时间,捕捉的地点和环境。”科普大V小鱼说,在后辈面前,他们喜欢分享和探讨,就算是在自己最拿手的专业领域,也不曾“高高在上”。
“两位老先生坚持了一辈子的经典分类学,其成果是公认的能完全经得起考验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新兴的研究方法和最新的分类观点也一直是兼收并蓄的。”吕植桐佩服他们的专业,也敬仰他们的谦和与包容。
从《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一卷发行之时到2022年底,学界又认定了不少新的属种,所以两位老人决定将第二卷拆分成两卷,内容上作增补。
在第一卷里,费、叶两人针对角蟾科基于传统形态比较学方法提出了一种分类体系,但后续有其他研究人员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给出了不同的结论。
“我这边刚好发了关于角蟾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和书中不同的分类系统。在第三卷中,对角蟾科的增补内容里,我也参与整理了部分物种。但在分类体系上,叶老师不太确定以哪一个分类体系为宜,所以特地征询了我的意见。”吕植桐认为自己只是基于部分基因片段得出的结论,虽然也结合了许多外部形态特征,但未来仍需更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而且他们的结论还有骨骼图作为有力的支撑,我深知这也是我的研究中所欠缺的关键内容。”于是吕植桐建议叶昌媛与第一卷的角蟾分类系统保持一致,这样前后也有对照。“叶老师采纳了,我们都没有强加自己的观点给对方。”

两位老人收到后辈送的七夕花束。毛萍摄
鞠躬尽瘁 留下遗嘱让妻子“坚持地工作”
去年三月,《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二、三卷正在紧张编撰时,费梁开始频繁呕吐,并伴随着剧烈的腹部疼痛。入院后,他被诊断为胰腺癌。
病情肆虐,把老人折磨得没法进食。四月,骨瘦形销的他怕时日不多,只要有意识,就一心扑在第二卷的书稿校对上。

病中仍坚持工作的费梁。费幼聪供图
按照费梁的意思,医院照看自己的工作全部交予儿女,这样就可以腾出时间给叶昌媛,让她踏实待在办公室。
“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子,两人能一起完成的就一起完成。”叶昌媛和丈夫达成默契,她加紧对照参考名录,仔细查看动物的评级有无变化,及时纠正。一遇问题,就致电费梁,隔空讨论,合力完成了第二卷书稿清样。
到了五月,仅靠输液维生的费梁仍然坚持着做第三卷的书目编排和骨骼图的精绘,想尽量少留一点困难给老伴。27日,在费梁失去意识进入ICU抢救前的三个小时,他做完了第三卷的样稿模板,也给妻子留下了嘱托:“你一定要努力地工作,细心地工作,坚持地工作”,叶昌媛含泪应允。
六月初,费梁与世长辞。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叶昌媛都不接熟人的来电,也谢绝任何拜访。
因为敏感的她,怕忍不住流泪。她才做完白内障手术不久,一旦流泪就“费眼睛”,进而会影响到专著的编撰工作。时间宝贵,叶昌媛一点都不想耽搁。
如今,叶昌媛的案头依旧堆满了资料。房间的格局未变,只是书桌那头,却空出了一块。电脑和手写板不见了踪影,只留用旧的解剖镜。
叶昌媛提到以前,工作重担都是费梁来挑,他会愁到睡不好觉。现在换叶昌媛睡不着了,但一想到老伴,她安慰自己,该克服的还是得克服。“不然,工作谁来完成?”
父亲离世后,费幼聪担心母亲,每天都接送她上下班。后来老人坚持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不用女儿操心。现在,就算偶尔加班至入夜,她也可以独自收拾回家。
费幼聪记得,在一次散步时,母亲突然说了一句:“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擦干眼泪,继续前行”。

两人办公室,只留叶昌媛一人。毛萍摄
熬得住苦 她带着嘱托继续与时间赛跑
叶昌媛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能扛,得益于年轻时候吃的苦。
“以前跟着小组去二郎山科考,白天考察好物种的栖息地,晚上就穿双袜子套双草鞋,去河里踩水采标本。”叶昌媛一会下水一会上岸,袜子湿了干,干了又湿。
野外科考像“打游击”,以道班为据点,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处。当时汽车少,前往下一个道班基本靠脚。叶昌媛肩挑一扁担,这头铺盖卷,那头铁皮标本箱。最难的是爬坡,她集中精力,默默给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小目标:300米、900米、1400米......直至翻过山头。

1963年叶昌媛,杨大同和储义珍在贵州印江县梵净山野外考察。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图
路走多了,苦就熬过来了。
但叶昌媛还是做好了“准备”,一边赶专著的进度,一边做好工作的交接,她要和时间赛跑。
这十多年来,老人的身体里陆续安装了3个心脏支架、1个心脏起搏器和1个人造股骨。去年七月,不幸跌倒后还做了第二次股骨颈手术。她变得更谨慎,平常走路会小心地避开不平整的路面。
她不知道能撑到哪一天。“费梁也没有料到自己的病情会发展如此快。”叶昌媛总想起老伴在生病初期,精气神十足,还给医生“打包票”:“我们家住五楼,但我一口气爬到六楼都没问题。”
好在叶昌媛不是一个人在前进,她的子女和后辈,成了左膀右臂。儿女是她的专属“秘书”,完成复杂一点的对接事务。有什么想法,或者需要统筹的工作,叶昌媛便告诉徒弟,成都生物所研究员江建平。
江建平团队的博士生张美华承接了骨骼图绘制工作。费梁在生前已经完成了所需标本的解剖以及部分骨骼图,余下的骨骼由张美华借助微型CT仪器进行扫描后,再作精绘。
事情一直在推进,今年上半年,《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二卷已顺利交稿,年底就能出版,叶昌媛心里踏实了不少。“等到第三卷正式出版,我就能真正睡个好觉了。”
六月,已经入夏的成都变得湿热。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华西坝园区内,生物研究所的搬迁工作已进入尾声,属于老园区的回忆和荣誉被打包到统一的纸箱,等待装车,踏上新的征程。
下午三点,回家午休后的叶昌媛再次步入大门,她穿着带简单花色的棉布衬衣,银色的短发梳得服服帖帖。一旁,搬家公司的卡车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着,吆喝声中,师傅们合力抬起柜子,放入车内。
叶昌媛来不及关注周遭的变化。和以前一样,她缓缓绕过被阳光暴晒的院坝,沿着楼房和香樟树撑起的阴凉,小步踏行。树荫摇曳,有风轻轻扬。

2021年致敬“四川百年百杰科学家”礼赞盛典结束后,二老共享荣誉。费幼聪供图
 下载文档
下载文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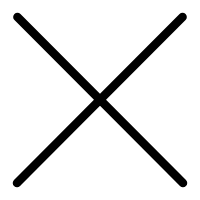
选择支付方式:
 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付款成功后即可下载
如有疑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ggq_bm后咨询客服